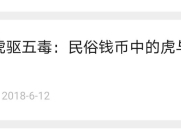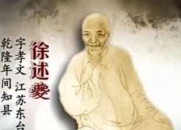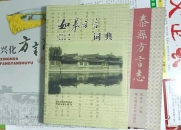在我老家门前,有条名叫小龙河的小河,虽不见书图典籍,更不比名川大江,却让我铭记终生。几十年了,它总是那么宁静,总是那么淡然,一直悠悠地流淌着。它也一直流淌在我的心中,默默地滋润着我人生的梦想,浇灌着我生活的期盼。
这条河流淌了多少年,没有人知道。
这条河流淌过我童年的快乐。

夏天的夜晚,小河岸边的芦苇丛中萤光闪闪烁烁,我和弟弟抓了好多萤火虫,装在一只洗净的墨水瓶里,吊在屋梁上当“电灯”。白天在小河里洗澡,清澈见底的水里小鱼儿成群结队地游,鱼儿叼得屁股痒痒的,有好多的虾在水草间蹦,父亲叫我逮活虾吃,“先吃头后吃尾,吃完了会舞(浮)水”,十岁的那年我在小河里学会了狗爬式(游泳),能钻猛子了。洗完了澡又上岸挑药草,把那种叫益母草的药草晒干了,拿到街上的药店去卖,好像是八分钱一斤,能卖得几角钱,又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铁道游击队》的连环画。

冬天的小河冻得结结实实的,我们几个发小可以在小河的冻面上比推铁环,比打陀螺。记得最清的是“四清”运动那一年,有几个贫下中农代表就是跟着工作队跑冻跨过小河,到我家“抄家”抬走了“家神柜”等衣物。那时我父亲是大队会计,被认为是“四不清”干部,父亲与工作队当场吵架,他用最粗鲁的话骂工作队,骂抄家的贫协代表,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阶级斗争的现场,第一次看到父亲从未有过的愤怒神情。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小龙河上的坚冰,越冷越冻越坚硬。
这条河流淌过我青春的苦涩。
那一年冬天我初中刚毕业,还不满十六岁,大队要搞小型水利工程,说是给小龙河裁弯取直,要给小龙河“脱壳”(拓宽),半个月的工程计划,生产队长说“我们六队必须十天完成”,因此家家有任务,户户出劳力,于是我也拿起了扁担泥篼子和大锹,上到了河工地。那时没有机械化,全是人力手挖肩挑。咦咦咦,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我和大劳力一样,也硬着头皮领了一段任务。
真是几天河工苦,胜读十年书。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紧挨着我一样挑河的是邻居王宏德,他说“你头三天挑下来,后边就好了。”那时我们小村庄的人有顺口溜:“男人的出路,一是当兵二是上窑厂”,王宏德曾经到山东当过王效禹的兵,当兵二十二个月后又回来上窑厂,但还是不行,生产队又把他从窑厂揪回来上河工。
就在我一边无可奈何忍耐着腿酸肩痛差不多是背扛泥担子,一边苦思冥想暗自要找什么借口逃离工地歇息的时候,大队通讯员在队长的指点下远远地朝我喊:“杨—永—进—,大队通知你去一下!”那时真的如同救了我的命。王宏德帮腔着说,快去快去!这一天真是我1970年冬天的第一个太阳,我在小龙河上迎来人生走向社会的第一屡阳光。大队决定我接任六队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富礼同志对我连说两遍:“六队的财务大权交给你了。”

小龙河 “脱壳”工程结束后不久,我做了两年时间的生产队会计。
现在,我每回乡下老家,总要在小龙河边走一走,静静地看着河水悠悠地流,不急不慢,还是那么的清,还是那么的不言笑,不腾欢,也不苟且,只是现在的冬天没有那么冷了,好多年都没有结冰上冻了,夏天也没有那么多芦苇了。有的只是一片宁静。
小龙河,永远安详宁静的小龙河!这种宁静伴随着我的激情,激励着我不断前行。但比起这条小河,年老的我还是常常感到这种宁静似乎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