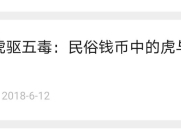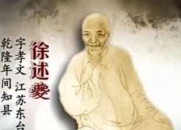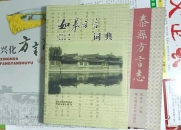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
三丫头认识我舅舅,一看我家来了上亲,顾不上自家做饭的事,一边着人去田里喊我母亲赶快回家,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我舅舅先进门歇歇。

张庆 摄 犹记从前的乡村生活,虽则物资匮乏,但邻里乡情对乡人的身心却多有补益。 那时每天三顿,乡人很少有守着家里饭桌的,都是装满饭后再搛上菜,然后捧碗出门。这一捧,有可能捧到巷口,也有可能捧到某户人家门口。其间不仅交流家长里短,还有饭菜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哪家做了稍好些饭菜的,他必定要将碗里的好菜匀给其他捧碗的乡亲尝一尝,碗里得到好菜的人必然客气地谦让:“你吃,你吃!”而此时分享的人必然会豪气说:“家里多哩,我再家去搛!”甚至还有换饭的,一个看着另一个的碗里说:“咋想得起来中午喝薄粥的?你个大劳力能挨到晚?”“早上粥煮多了,放到晚上怕馊。”问的那个人其实晓得那时农村吃粮紧张,很多人家舍不得煮米饭,吃顿白米饭算是奢侈的。这时就不由分说,一把抢过对方的粥碗,把自己的饭碗递过去,嘴里还煞有介事地来一句:“正好我口里干,换格哉!”这样的场景时常在邻里间上演。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有乡亲家到了客,不免去称肉买鱼好好招待。烹调的香气常会引得邻家的孩子在门前转悠不停。大多数主妇往往会在忙好饭菜后,拿只小碗装上点饭和菜,然后颠颠地送到邻家,给孩子们杀杀馋虫。同在一个村,有时这个生产队里分了点瓜果梨桃或是菱角,那么其他生产队的乡亲因为转送也可以尝到,彼此都以分享为乐。 记得那年我远在东台时堰的二舅来黄尤村,紧赶慢赶,起个大早的舅舅到我们庄上时已经近午了。恰好在田间的阡陌上遇到急匆匆回家做饭的邻居三丫头。三丫头是我本家大大芹广的老婆,我喊她大妈。三丫头认识我舅舅,一看我家来了上亲,顾不上自家做饭的事,一边着人去田里喊我母亲赶快回家,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我舅舅先进门歇歇。那时邻居家的钥匙放哪,大家都很熟悉,碰到阴天下雨,有人赶回庄抢收外面晾晒着的衣被,乡邻们都会主动帮还没来得及赶回的邻人收起衣被等放进门。三丫头带我舅舅回庄,摸出我家钥匙开开屋门,迎我舅舅先进屋,然后打开家神柜抽屉找鸡蛋打蛋茶,发现我家只剩两只蛋,又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赶回自家拿来鸡蛋凑数,随即下灶烧火一顿忙活,烹煮出甜甜的蛋茶让我舅舅先填填肚子。 待闻讯赶回的我母亲带着沿路买的鱼肉百叶到家时,我舅舅已经吃过蛋茶,在堂屋里气定神闲地歇着了。三丫头又相帮着我母亲杀鱼、择菜,然后蹲到锅灶前烧火,让我母亲专心在灶上掌勺。不一会饭熟菜香,三丫头这才直起身,拍拍双手,掸掸身上的草屑、尘灰,急匆匆赶回家忙中饭。 这种淳朴的乡情一直延续到分田到户的头几年。每到大忙,那时的乡亲时兴拌工,就是几户人家的男女劳力集中起来,轮流去各家干活,主家只负责管饭,不谈工钱。虽是大忙,但管饭一点也不搭浆,那时刚刚富裕起来的乡亲尤为慷慨大方,大鱼大肉自是管够,还有成箱的汽酒、果子露,人人都敞开肚皮吃喝,然后到地里卖力地大干。 时过境迁,当年那些温馨的场景竟成了珍贵的记忆。现在的人们虽没到“以邻为壑”的程度,但相互的走动变得越来越少,家家都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收到一个赴家宴的邀请,那必定不是因为主家图省钱不去饭店,而是对客人的一种更高的礼遇。 从前村里只要有人家拌嘴干仗,恨不能全村的人都赶来相劝,战火于是及时熄灭,矛盾得到及时化解。但现在都是关起门来吵,哪怕你听到乒乒乓乓的摔打,犹豫再三也只能作罢——谁知道人家烦不烦你多管闲事,就不要狗拿耗子了。 当年的那种淳朴的邻里情,真让人怀念呢!
来源:东关街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