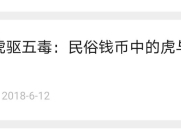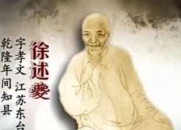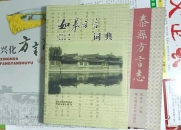中国大运河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半叶持续完成的巨型人工运河工程。它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省(市),涉及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河道总长约3100公里(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其中主线长度约2681公里。它经历过运输河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长1011公里)、国家文化带及文化公园几个阶段。今天它具备生活、生产、文化、运输、供水、水利、生态、旅游、景观等综合性功能。
京杭大运河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大运河身份的变革:从经济性到文化性
21世纪以来,文化战略成为世界性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适应这一形势,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身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化,即从一般性运输河道转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
2005年12月,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三位专家联名致信大运河沿线各市市长,呼吁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58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提案,呼吁启动对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6月,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启动。2007年9月,“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在江苏扬州挂牌成立。
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评价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列入世界遗产的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河道27段,遗产点58处,涉及沿线8个省市的27座城市,河道总长1011公里,约占总长的1/3。
国家高度重视大运河的保护利用,要求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2017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2017年6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2017年6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济南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贯彻国家领导指示,以大运河为核心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使之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标志。
2019年3月26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2019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于2019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执行。包括江苏在内的大运河沿线各地与“规划纲要”及“建设方案”进行对接,制定充分体现区位特点优势的高质量实施规划。“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所处历史空间与我国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及雄安新区、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带、淮河生态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一带一路交汇地等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历史意义、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国家级以文化为引领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项目。
(二)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局域性运河阶段,从公元前486年前后邗沟、胥河、古江南河(丹徒水道)、黄沟运河(沟通泗水与济水,入黄河)、鸿沟等开始,一直到隋代之前。主要涉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之间的运河;浙东运河在这一阶段也已成形。还有西汉吴王刘濞开通的“东邗沟”、西汉的漕渠、东汉的阳渠、三国时期的破岗渎、越国山阴古水道、西晋西兴运河(沟通钱塘江与曹娥江)等。
第二个阶段,全国性大运河形成,历隋、唐、宋三代。北及涿郡(今北京),南至明州(今宁波),西通长安(今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等。包括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盐河等。
第三个阶段,全国性大运河的进一步发展,京杭大运河阶段。历元、明、清、民国到今天,从北京到宁波,包括通惠运河、北运河、南运河或御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等。这一运河又成为当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运河源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这和今天的苏州有关系。《左传》记载,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滥觞。公元前482年,吴人又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
战国时,魏国开凿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连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汴、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其中通泗的运道成为后来汴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它最早把江苏徐州纳入了后来的大运河体系。邗沟、菏水、鸿沟等局域运河的开凿,使长江、淮河、黄河、济水四渎得以贯通,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的区域性运河体系。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中国转移,为巩固统一国家,必须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8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网。
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标志着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由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高达600万石。北宋运河系统的发达,运河建设的成就,漕运的繁荣,漕运体系的完善,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
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发展受阻,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在强敌压境的态势下得以偏安不辍。
京口闸遗址出土元青花海龙纹香炉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要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一是济州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长150里,引泗水、汶水为水源。二是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连通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三是通惠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引大都白浮山泉为水源,自通州至大都城,仅50里,但是开河总长达160里,其间置闸坝20处。通惠河的开凿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开京师金口河,自通州南高丽庄起,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全长120里。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近代以降,大运河进入衰弱时期。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长达700余年的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也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年),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自此,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终结。
民国初年,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后因军阀割据、财政匮乏、技术缺失等因素而陷入停滞。抗战时期,运河区域位于沦陷区,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治理,甚至很多河段已淤塞不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仅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一直到20世纪结束,人们对大运河的价值认知,还是停留在运输、水利等原始功能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才获得改变。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建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生、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认知
第一,大运河是中国的政治河、经济河、文化河。
首先从政治角度去看,它是一条“政治河”。大运河的第一功能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国家文明,包括军事力量调度功能、供应首都中央物资所需的漕运功能等,是为了国家统一、国家稳定、国家治理,为了不同区域的相互整合、沟通和互动,为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与凝聚,为了国土安全等。为此,历代大运河的开凿、修理、管理等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予以主持,如夫差、杨坚、杨广、忽必烈、朱棣、康熙、乾隆等。在唐朝中期之后,大运河就成为支撑首都和中央运转的生命线。
当然,大运河也是“经济河”。包括国家经济和民间经济,如大运河及其连通的自然河道沿线和沿海区域资源的开发与流通,盐、渔、粮、丝、棉、茶、瓷器、木材、药材、砖瓦,各地土特产餐饮业、娱乐业、服务业等都在运河沿线进行生产交流贸易,多种新的经济业态得以成长,大批的城市、城镇得以成长,农业渔业得到开发,税收得到保障。大运河是推动我国国土“胡焕庸线”现象形成的重要力量,这条线已经很少被提起,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说大运河是“文化河”,是指大运河沿线的各种文化遗产和文化成就,如城市文化、集镇文化、建筑文化、手工艺、教育、雕版印刷、书画、科学技术、文学、园林、饮食、戏曲、音乐、故事、民俗、宗教、文化人才等大量涌现。大运河沿线交通的便利、信息的交流、经济的繁荣、人才的来往、物资的流动、文化的碰撞都带动大运河沿线文化趋向发达,使之形成中国文化的富集区。
第二,大运河使得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与草原丝路、天然运道和人工运道、经济基础和文化创造相互沟通、融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
从隋唐开始,中国的首都如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都不可能离开大运河,南北政治中心必须与大运河相连接,才能获得首都的生存保障和国家政治中枢正常运转的条件。海上丝路中的遣唐使、元代马可·波罗、明代利玛窦和苏禄国王、清代马嘎尔尼等海外使者无不与大运河发生关联。中国外销的瓷器、茶叶等商品也多由大运河集散外运,中外沉船考古,如印尼黑石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等,可以充分证实这一历史过程。
大运河把唐代青龙镇、黄泗浦、掘港、扬州涟水、楚州、海州、登州、宁波,宋代杭州、温州,元明清的上海、南京、天津等通海港口城市或集镇组织在一起,形成海上丝路的大通道,与陆上丝路相互连接,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汇聚通过大运河得以顺利实现。当然这种沟通也有长江、淮河、海洋的广泛参与。

第三,大运河得以成功,是由于中国先民充分利用了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运道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特征。
一是中国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如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人工开挖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正可把它们打通连接起来,形成东西、南北天然运道和人工运道相互交织的最便捷的运输体系,首都—运河—天然运道—地方性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每一个集镇和乡村,这是一种贴近实际、高效低价的运输工程创造。在不同运道的连接之间,涉及许多水利水运工程技术问题,在每个接点上,不同流域的分水岭处,都有诸多的智慧性工程杰作,如淮安、扬州、镇江、仪征、汶上等地保存的相关水运工程遗产特别丰富。
二是湖泊与大运河的紧密关系。数千里的大运河在不同的地段要保持水流畅通,离不开特定区域可以提供补水、调水的“水柜”,包括自然的湖泊或者是人工的湖泊,在早期阶段,有的运河河段就在湖中通行,人称“湖漕”。
大运河沿线从最北端的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到最东南端的宁波市东钱湖,沿线湖泊有70个左右,比如洪泽湖、太湖、南四湖(微山湖等)、鉴湖,还有山东东平湖、宿迁骆马湖、苏北高邮宝应白马湖、扬州瘦西湖、丹阳练湖、杭州西湖、萧山湘湖、绍兴东湖等。有的是人工湖,有的是天然湖,有的是半人工半天然湖,有的干脆就是借湖行运的“湖漕”之湖。这些湖泊与运河相生相伴,一般都有为运河供水或为运河滞纳洪水的作用。
三是大运河与海运的结合。如宁波港口、太仓港口、上海港口、天津港口、扬州港口等都离不开与大运河的联通。为此,大运河作为人工河流,之所以有那么大的作用,那是它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系统,支撑着一个大国的物流体系。
同时,沿着水运道路,还有陆上驿道的修建,使之形成水、陆相辅相成的行水供水系统与交通系统,使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水陆皆备的交通命脉,使之在隋唐至明清长达1000多年时间里成为中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当然,此前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至南北朝等时代积淀形成的各区域文化及局域性运河恰恰为大运河时代的到来、为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动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大运河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力量。
中国5000年文明进程中,早期的中心还是在中原至关中的区域。但到了唐代,出现“扬一益二”,江南税贡始占主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明清江南区域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民国成为胡焕庸先生发现的“胡焕庸线”所概括的现象,在这条线的以东区域,大运河正居其中。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等国家经济文化格局的出现。
大运河一线的城市带即从北京到杭州、宁波,仍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创造这种现象的核心力量即来自千年流通的大运河。今天的南水北调东线、贯通中国南北的运河生态大走廊仍然在大运河一线。这也正是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所能找到的历史创造与现代文明的高度关联、古今一体,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让文化遗产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