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桥烧饼/涨烧饼/东台冷锅饼

董小潭长篇小说《天滋》首发式在泰州杨延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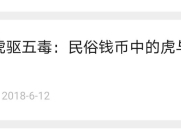
童骋 | 虎驱五毒 端午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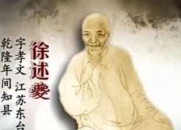
张永辉 | 闲话盐城名人—徐述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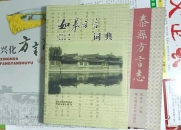
夏俊山:从“腌饥菜”说开去

徐友权丨小镇端阳

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评滨海县淮剧团

翁太庆 | 河边那棵楝树

夏俊山 | 学习郑板桥用风骨撑起人生

“歌唱延安 礼赞时代”诗歌征文颁奖庆典暨

梁实秋与汪曾祺,美食美文大PK

高汉荣 | 老兵义工的助农公益之路

一个杭州人17岁主政盐城,儿子和女婿各建了

童骋 | SA25/5加拍(#52)·异型花钱选赏

崔月明 | 一场雨过后

民国时期东台茶馆业的“灶君会”

夏俊山:我希望范曾也来看的名人故居

童骋 | 山塘街 不了情
《溱湖断想》,真的很美2024-1-10 17:46:20 69147 0 |
| |
|
|
|
昨天,本公众号登载了【史海钩沉】《黄桥烧饼歌》
5月28日上午,长篇小说《天滋》首发式在泰州海陵
在民俗花钱里,驱五
朋友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盐城名人叫徐述夔。徐述
从“腌饥菜”说开去夏俊山5月20日《姜堰日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