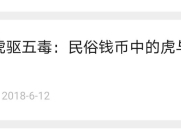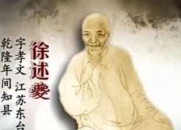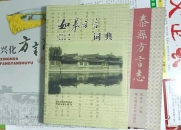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
大量北方人口进入,里下河逐渐形成“人多地少”的局面,进而推动了本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在射阳湖区有过两次设置官屯的记录,其中一次是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位置在射阳湖以西;另一次 是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位置在射阳湖东部洼地,也就是兴化东乡、东北乡一带。

射阳湖东部洼地一直延伸至海滨,潮灾是这一区域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唐大历年间(766 -779),出于屯田的需要,在兴化东部海滨筑成了一道捍海堰,主持修建者是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 所以称“李堤”。李堤修成之后,堤内农田收成颇丰,有往常的10倍之多,因此又称“常丰堰”。“常丰堰”大致沿东冈一线修筑,具体位置已经难以考证,《光绪淮安府志》含糊地说:“自楚州盐城,南抵海陵,亘百余里,以捍海潮。”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兴化东乡、东北乡,都是在“常丰堰”屏护的范围之内。如前文所说,射阳湖东部洼地的初步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末年的兴化“千人湖”。不过受潮灾及土壤盐碱度的影响,这一区域的农耕环境还比较恶劣,农业经济也相对落后。“常丰堰”修筑之后,这一地区得以远离潮灾侵袭,土壤进一步去盐碱化, 由盐碱地转变为适宜稻作的熟田,兴化东乡、东北乡因此成为里下河主要的粮食生产地之一。按明代人的说法,唐代时兴化已经设置“昭阳镇”,说明至唐代中后期,兴化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有较大发展。另据兴化海南镇北蒋村出土的船形“田”字银锭推断,唐代中期在兴化东乡设置有行政机构,很可能就是管理屯田的“田官”所在地。

唐代船型田字银锭
“安史之乱”以后,京师给养完全依赖于淮南和江南的漕粮。据《新唐书》记载 :唐大历年间,宰相刘晏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即是从淮南转运粮食至东都洛阳,“引海陵之仓,衣食巩洛”。《大唐京兆韦公墓志铭并序》也记载:“江淮晏如,而海陵之仓已□於京廪矣。”这里的“海陵之仓”,是设置于海陵县境内的众多官仓的总称。官仓里所储积的米粮,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射阳湖东部洼地的官屯,正是这些米粮的外运,促成了兴化水运网络的初步形成。兴化境内的东西向河流, 如蚌蜒、车路、海沟等河,其具体的开浚时间已难以确认。唐王朝中后期,在淮南盐粮赋税日显重要的背景下,以设置射阳湖官屯为契机,官方利用兴化境内一些东西向的天然泄洪水道,拓宽加深,使之成为一条条人工运河,用以连接高邮运盐河、山阳渎、南北大运河、东邗沟等漕运要道,由此形成兴化水运网络的雏形。这一说法大致可信。陵亭镇位于蚌蜒河、卤汀河、南官河、盐邵河等众水交汇处,是兴化通往扬州、泰州的必经之地。陵亭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唐代中后期,唐代中后期陵亭镇名为“陵亭场”,行政级别较高。唐大中七年(853),进士出身的海陵县丞张观,受淮南节度使杜悰委派,出任陵亭场主官。《全唐文补遗》记载:(张观)总陵亭场务,操断逾年,颇更积弊……俾其曹吏乡里,咸畅公清之长;囷仓帑藏,皆无逋缺之非。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唐代时期关于兴化的唯一文献记录。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陵亭场不仅有一套行政机构,而且还设置有官仓,这座官仓里所储 存的粮食,很显然是来自于蚌蜒河下游,也就是“常丰堰”所屏护的兴化东乡、东北乡一带。

除收储米粮之外, 陵亭场还承担着另外一项重要职能——征收盐税。唐代中后期,扬州海陵监共辖有8座盐场,统称“南四场、北四场”,陵亭场是否在8场之列,由于史无记载,也就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陵亭场,已经是淮南地区的一处经济重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勉强维持了100多年。唐王朝能够从战乱的废墟中重新崛起,所依赖者有二:一是江淮财赋,二是中央禁军。要言之,以丰厚的江淮财赋供养强大的中央神策军,以此威慑地方藩镇,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基 本国策。江淮财赋主要出自于淮南盐税,陵亭场作为盐税征缴的场地之一,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杜悰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堂兄,贵为驸马都尉,官至宰相,是唐王朝十分倚重的外戚。杜悰的祖父杜佑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曾经在扬州开展大规模的军屯,“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杜悰委派自己的心腹张观主政陵亭场,目的是越过地方州县,直接将陵亭场征收的赋税收归己有,从而延续其祖父杜佑“以财赋供养军队,以军队威慑藩镇”的治理模式。晚唐时期的陵亭场,商旅云集、舟船往来,运盐河边一座大庙濒水而立,大庙名为“法华院”,建于唐咸通四年(863)。南宋《舆地纪胜》记载:法华院“在兴 化县南陵亭镇,唐咸通四年置”。寺内另有一口铜钟,钟声十分清越,钟上镌刻有铭文:“唐乾宁中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