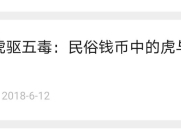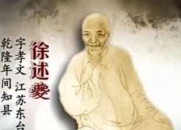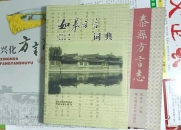野草虽野,它默默地生长野外,从来无需人类的一点关照,但它对人类和世界却有着一颗温爱之心。有的野草不仅能吃,同时还以别样美丽的风姿装点着生动的世界,与树木河流一道产生源源不绝的氧气。作者在塬上的老家生活了十八年,其生命的底色与野草、庄稼、牲畜、河流、旷野一路相伴,在蓬勃的生命景观中早已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至深缘分。野草是大地之子,也是人类的挚友。狗牙根、牛舌头、猫儿眼、车前草、野燕麦、野豌豆、蒲公英,不用任何词语修饰,把本文中近三十种野草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幅幅五彩斑斓、令人迷恋和遐想的生态图景。大凡与这些野草打过交道的人,手掌心和指甲缝里都留下它们难以洗涤的色彩。如果像作者一样,很小的时候便了解和熟稔它们的品性及价值,阅读这一种又一种野草的名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口齿生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生理和化学反应了。
本文的调性具有独特的西北风味。我以为它是陕北高原硬朗汉子面目下的文人柔情,与烟雨迷蒙的柔美江南形成了语言格调的互文。对专写挑猪草的散文,我阅读了一些,但像本文把大地上所有的小草写得如此种类繁多,像金陵十二钗呈现鲜活样态的,不多。某些大作家、散文名家借物言志的散文,读者尚未共情,自己倒先调动起昂扬的情绪,并用空洞的辞藻予以装饰,从而钻进自己设计的情感圈套里出不来,结果读者还是捧读文章之前的读者,与读者并未形成情感的联动和呼应,距离越来越远,更别说共情共鸣了。这篇文章的抒情是以密密匝匝的寻草、挑草和周围的大地风物一同体现,形成情感的真实可信和酽酽的浓度,拨动了读者埋藏心间的曾经的岁月之弦,从而引发自然而然的联想和共鸣,形成阅读效果的音乐和声。
《长成一棵草》,处处写草,通篇说草,朴素的浪漫主义,表达了作者对野草的深情眷恋。在陕西,在江苏,在江河湖海,野草的品类实在太多了。它们是大地上的生灵,是丰富复杂自然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映射:有毒的,无毒的,开花的,结籽的,趴地的,凌空的,高调的,沉默的,离离塬上草……作者写尽了各种生命样态的野草。他是现代社会令人艳羡的野草专家和幸福的爱草人。
作者的抒情是隐忍节制的,没有嗯嗯啊啊的滥调,但字里行间又充满着浓郁的情感。它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是我与野草之间寻找一一发现一一采摘的寻常日子的生命叙事。掩卷沉思,本文就是一棵充满汁液的鲜活的野草,仔细咬嚼品尝,丝丝甜味才能在你舌尖跳跃。
此文仿佛一株青翠鲜活的秧苗,充满了汩汩涌动的张力。
当下的农村还用人工栽秧吗?不是早就实行机械化了嘛。机械化插秧的,有,但不充分,人工栽秧的地方依然大大地有啊。不要说是沿海的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在中原、西部、南方、北方,完全靠人力栽秧的更多。栽秧苦,每天都是“两星一昏”地黏在秧田里。所谓两星一昏,就是每天早晚披星戴月下田,中午在田埂上胡乱扒几口饭,晚上月亮和星星升上了天空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阴天下雨天还好,若是晴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蚂蟥钻肉吸血,捏着秧苗插入泥土的大拇指和食指被泥水长时间浸泡而发白,变皱,像水泥一样的泥巴钻进指甲尤其疼痛难受。连吃饭抓筷子都抓不住,上厕所解裤带也不利索。关节僵硬了啊!至于安装在肩膀上的脑袋,那才叫真正的变大!栽秧的身姿是屁股朝天撅着,脑袋面向浅浅的水面,插一棵秧点一下头,插一棵秧点一下头,这种九十度的弯腰鞠躬,一时三刻的还行,半天,一天,一天十二三个小时,人的整个脸就浮肿了,眼睛躲进了肉里,成了一条缝。这是血流涌入所致。在1970年代,一提到栽秧,我就害怕,心就颤抖。人在劳累之后,食欲也大打折扣。再美味的饭菜,不想多吃。吃不下。因此,栽秧的那十天半个月,是吃不好,睡不好,浑身疼,遭大罪。我曾经当着乡亲们的面说过,这种日子,不如坐监,不如枪毙。人们听了哄堂大笑。村庄里的人至今还在笑话我。沈玉年的文章最可贵之处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没有一味地唱赞歌。全篇没有用什么形容词,而是客观地描摹记录。我称其为黑白片的纪录,或者是初期电影的默片纪录。作者的思想没有强加于人,而是融汇在叙述的场景和人的心情里。这种朴素的文字表达,叫人看了很舒服,更易令人共情和共鸣。
现在的散文,甜腻型已渐渐地失去了阅读市场,非虚构的质朴的不加任何雕饰的文章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根本原因还是真和假的问题。真的就是老实的,假的就是滑头的。犹如做人,社会上欢迎的还是说真话的老实人,满嘴跑火车的说假话的,甜甜软软的文章,人们早就生厌了。
沈玉年的文章给我们上了一课,她的这棵秧苗,激起的文学和社会涟漪是经久不息的。
距离,缘分,信赖,是读罢本文后脑海里产生的三个关键词类别。
佳木斯,扬州,一个是常年白雪皑皑森林覆盖的北方边城,一个是被总书记称为好地方的南方佳丽地,在祖国的版图上各自呈现她的富饶和美丽。自从有了手机,有了微信,人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缩短了,天涯若比邻是在地球村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人间活剧。但是,也正因为手机,正因为微信,人们频频上当受骗,失去钱财乃至更大损失的案例太多太多。但是,人间总有真情在。这个李贞琴,鬼使神差,瞅着空档摸鱼儿,摇上了帅哥看不中,摇上了美女也不加,偏偏喜欢上了这个网名叫愚公的佳木斯老伯。这个毕老伯,女儿早亡,孙女患病,自己身体也有疾,与老伴和孙女在祖国北方的林场相依为命,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唯一的不安分便是在林场值班的时候,拨弄手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作者在虚拟空间相遇了,从此一口一个丫头,各种蘑菇洋参等等山珍往扬州快递。现代社会,一片热热闹闹。拨开表面泡沫,人的内心又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唯有通过读书、娱乐、社交来填空和消解。
人与人相知相见,是要有缘分的。聪慧美丽的扬州姑娘李贞琴和尝够生活艰难困苦的毕老伯竟然在那一刻的渺远空间不期而遇。这是上苍赋予彼此的善缘,我相信南北双方定会好生珍惜,用心地又是自然地去维护这种难得的友情,给人生增添美丽的一笔。
作者去了佳木斯,大包小包的东西没有详说,这是她的为人风格和境界使然。她和妹妹不会空手去的,就像他们从佳木斯回来不会空手而归一样。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好看和期待了:李贞琴请毕老伯一家来扬州看看这是不用交代的。人活在世上,不就是以人心换人心吗?不就是幸福快乐吗?谁愿意被社会抛弃和碾压?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毕老伯一家那天到了扬泰机场或者扬州高铁,李贞琴一家喜气洋洋地等候他们。这种故事反映了一个地域的温良和文明,以及平民大众的精神表情,它像陈年老酒喝在嘴里醉在心里,很值得反复咂摸。
周旭,一个思乡恋家,从省级机关退休的老文青。
来源:扬子江文萃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