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楔子
已退休在家16年的顾德昌,成了地地道道的“弃工从农”型人物了。
他虽然每月可以领取一笔算不上丰厚,但也算比较稳定的退休金,维系着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生活。但与他原来厂里安享晚年的“半家户”所不同的是,他的家庭经济基础却不允许他随意撂去肩头上的那副重担。因此,他退下来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自在。诸如,老婆常年患病,问医求药不菲的花销;自己居住多年破旧失修的茅舍迫切需要翻新;相继操办三个待嫁女儿的婚事等等。掐指算来,这一笔笔叠加起来的钞票,对他来说犹如天文数字,不得不使他仍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身耕作和节衣缩食的生活。当他终于将这些大事逐一了结之后,他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仿佛是在一眨眼的工夫之间,他脸上带着几许欣慰,也含着一丝遗憾,在老伴去世10年后的同一日,撒手人寰。终年70岁。
人到七十,当属古稀。按当地农村的风俗,即使家里再穷,哪怕举债也要为三天丧事办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而前来顾家凭吊的族里亲戚,却显得稀稀落落。特别是顾德昌平日所寄予无限期待的工作单位——东方机械制造厂,也早已破产倒闭,当年的领导及同事,都树倒猢狲散,消失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未免使顾家门庭显得有些冷落和凄楚。
村里有人认为,这与顾德昌性格的冷酷、古怪、孤僻;平日里为人处世的吝啬、傻憨、呆萌而不近人情,有着极大的关联。只有他的三个女儿、女婿,正在尽心竭力为他惨淡的人生,修正一个并不是那么圆满的句号。还有他的三个外孙女,责无旁贷地替代着本该由孙子履行的义务,肃穆地站在灵前,为其守灵尽孝。
逝者脚边的“长明灯”,在忽暗忽明地闪烁着。恍若是他的幽灵在一声高、一声低地叹息着;又好像他那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在询问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为何如此暖冷炎凉;更像他在那边的世界里,不停地眨着眼睛,窥望着这70年来,人间的风风雨雨和世事沧桑。尤其是他那段曾经的热火朝天而刻骨铭心的工厂生活,与自己贫困窘迫的家庭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比照。
所有这些,似乎给逝者在黄泉之中,留下了永远都抹不掉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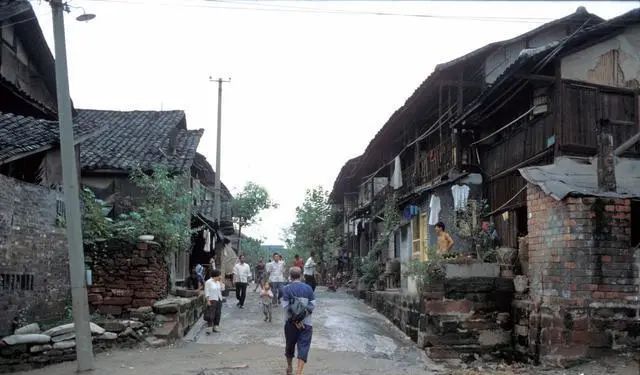
(一)
顾德昌在家中排行是老大。为此,电焊班里的兄弟姐妹们都嚷着叫他“昌大”。又黑且瘦的昌大其貌不扬,却成了班里的“新闻人物”。他是占全厂职工总数约百分之十的“半家户”之一,不但外貌丑陋猥琐,而且说话很冲,很难与人交流沟通。用不着仔细端详他的容貌,光看他双眼下面那只又高又大的鹰钩鼻子,一准让你感觉恶心而咽不下任何食物。如果让他到哪个影视里扮演反面人物,一点儿都不需要化妆,马上就可以入镜。
有人说昌大特别“抠”,把一分钱看成磨盘那么大。
有一回,班里一个外号叫做“幽默大师”的人,出差从外地带回一筐桃子,让大家尝尝鲜,每人4只,只收成本两毛钱。可昌大却把头摇得像个扑啷鼓似的,连连喊不要。“幽默大师”指着手上的桃子说:“昌大,这水蜜桃可是正宗的无锡阳山特产,它由甜润清澈的太湖水滋养成熟,咬一口准能甜掉牙。当年孙悟空吃了,到西天取得了真经,你尝了之后,必定吉星高照,日后准会财源滚滚的!”昌大却绷着那张刀砖般的脸说:“尝什么倒头梦啊!去你的吧,瞧我这副腻腻歪歪的样子,哪有什么吉星在头上高照着我?更何谈什么地方来的狗屁财源?”一句话,说得正在嘻嘻哈哈、兴高采烈的大伙都尴里尴尬的。
为此,班里有人说他抠过头了。如今,两毛钱连3岁的小孩都嚷着嫌少,你昌大这做派,分明是撒泡尿也恨不得要拿只粉筛来过滤一下,看看有没有从身上漏掉些什么。
也有人认为他非常“憨”,总喜欢做丢西瓜捡芝麻之类的蠢事。那天,厂里每人发了一顶布料是中长纤维的长舌工作帽,质量那叫个妥妥的好。他没戴,搁在一张凳子上。不知是哪位粗心的女工一屁股坐在上头,被他视见后,好比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咆哮着从她的臀部底下抽出帽子,恶狠狠地往火炉里一扔。班里的人看了都失声大笑,而他却瞪着一双绿豆眼说:“你们这些家伙懂个俅啊,谁看见过女人爬到屋顶上去吗?要想过好日子,就不能这么糟践……”一席话把大家逗得更欢了,他却脸红脖子粗地争辨道:“这是我的自由,我高兴嘛。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奈何我不得!”
日子本就过得窘迫困难,还又被他过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