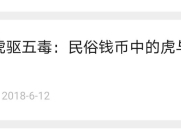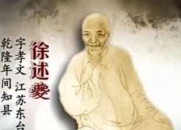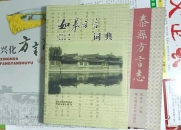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
母亲,最是了不起的名词,也是生命中最美的词语!近几年,也写了一点点东拼西凑的散记,笔下有关母亲的文字却几乎没有,提及母亲的少之又少,仅是偶有出现过这个字眼,但,从没浓墨重彩地描述过。 也许是从遥远的那声啼哭开始,从眷念那温暖的怀抱开始,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无微不至的关注开始,却足以用世间最华丽的词汇来形容她,那就是母亲! 我经常回家,看看那片田野,摸摸那座横卧庄前的水泥长桥的栏杆,闻闻房顶弥散的炊烟,再听听母亲拄拐的笃笃声。 在稻花飘香的气息里,处处布满母亲的皱纹,阳光洒满小院,渗透了母亲佝偻的背脊。 母亲老了,糖尿病死缠烂打母亲几十年,并发症使得母亲的双眼几近失明!椎间盘突出手术让母亲再次顽强地站了起来。每次回到家门口,咚咚的脚步声,亲切的呼唤声,听到声音的母亲这才知道,儿子回来了!母亲欣喜地拄起拐杖,布满皱纹的脸庞顿时舒展开来,于是,颤巍巍地从凳上吃力地站了起来,摸索着朝我站着。母亲经常唠叨我们兄弟俩,让我们带她去医院鉴定眼睛,能否帮她办个残疾证,这样就可减轻我们弟兄俩的经济负担,每次哥哥都一口回绝。这般年纪的老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毛病,不要给政府添麻烦!并且保证,有病帮她医,常年买药给她,让母亲安心在家,有事电话,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回!现在回家,母亲再也不提残疾证的事了。 萧瑟的秋风里,吹拂一个长长的思念和牵挂。我又回到了母亲常年厮守的老屋。南北贯通的老巷,长不足四十米,宽约二米,老巷里曾经住着四户人家,老少近乎三十口。而今,有举家迁徏亦或外出打工,寂寥的深巷里,仅剩母亲一人!苍茫之中,我回家唯一能够触摸的就是这条老巷,依旧保持着往年的淳朴,单调,干净。这条被母亲走过千万遍的巷道,如今让我感到陌生和落寞。母亲虽然不被秋风传诵,但她还坚守在这条不让巷口空寂的老屋里,时间过了很长很长…… 母亲老了。一辈子要强的母亲,和父亲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有近六十年的岁月里,也是一直强在嘴上。母亲经常和父亲吵闹,经常是母亲因为一点点的生活琐事就唠叨个不停,最后总是父亲的不是而收场。后来,吵了半辈子的父亲不幸离世,母亲稀里哗啦地哭得一塌糊涂,哀号声中夹杂着无限的眷念和不舍,母亲宁愿自己替代父亲,让他活在世上! 母亲老了。虽是多病缠身,仍坚持一个人坚强地守护着那座乡间的老屋,好似屋里藏着一笔不菲的财宝,生怕丢了。母亲常说,金旮旯银旮旯,不抵自家的穷旮旯。随着年龄递增,母亲总会感觉脚下的路越来越长,楼梯越来越陡,声音越来越小……有时,母亲请乡邻电话给我,我仔细聆听,往后每一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必须要回家。我一想,母亲说得很在理,死者为大!这是乡里人家的大节,蕴藏着血浓于水的故园之情。清明是绿叶对根脉的一种眷恋,更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溯自己精神源头的寻根之旅。母亲老了,一辈子从不放心别人做的事,母亲再无能力操劳了,电话里,听得出体弱多病的母亲有多么的惶恐和无助。 母亲如灯,照亮了我们姐弟三人前行的路,给我们行走人世间的力量和勇气。 母亲老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水乡深处一隅的小庄舍上,一个孤零的身影独守一巷的幽静,守着老屋和一帧儿孙们的照片,那是母亲长久以来的守望。
作者简介:

陈凤如,兴化荻垛人。70年生,农民,喜欢用文字书写水乡风情,田园风光,一草一木,泥土芬芳。
来源:阿紫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