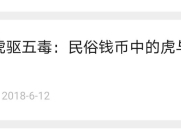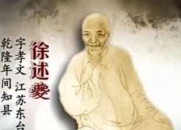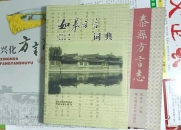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
1985年3月11日。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专门发来慰问电,高度评价和赞扬我师“三八”女子救护队是“和平事业的保卫者”、“八十年代的娘子军”。全国妇联授予“三八”女子救护队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三八女子救护队”整装待发(丹旗 摄)
临战训练期间,师党委决定成立师炮兵团“三八”女子救护队,由全师抽调的28名女军人组成。她们年龄大的42岁,小的才17岁,其中12人当了妈妈。在队长秦蓉、指导员赵丽君的带领下,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怀着对祖国赤诚的爱和对战友深厚的情,既当医疗队,又当宣传队,先后25次冒着炮火上前沿抢救接运伤员,共救治伤员102名;97次到连队送医送药、演出节目, 为阵地干部战士巡诊1561人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从老山通往船头地区,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那盘山而上的地方,便是许多战友特别是驾驶员心惊胆战的“三转弯”。官兵们把它称为“鬼门关”,这是越军火力重点封锁的地方——在长达不到5公里地段上,越军曾经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炮弹,把成片的橡胶林炸成一堆柴火,林场职工的住房也成了废墟,许多战友就倒在这里…… 然而,就是这个地方,“三八”女子救护队就驻扎在这里。起初她们当中也有胆子小的同志,听到炮声捂耳朵,看到伤员闭眼睛。通过开展“学英雄模范、想前沿战士”活动,大家懂得:战士们英勇无畏,不是先天就有的,为祖国甘愿献身的无畏精神来自思想的升华和战火的锻炼。因此,大家抱定一个决心:向前沿干部战士学习,不怕流血牺牲,在战火中打出八十年代女军人的英雄风貌。

“三八女子救护队”在前沿阵地救护伤员
化验员季悦,丈夫是战斗在一线的步兵团副团长,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季悦也被安排在机动组,要经常到阵地前接后送伤员,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夜深人静时,她拿出不满周岁孩子的照片久久凝望,多次想到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更不能没有母亲,也想过自己一不是医生,二不是卫生员,有理由调换工作。但她想得更多的是前沿战士们浴血奋战,为国献身的英雄壮举和军人就意味着牺牲的崇高信念。战争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用录音机给孩子留下了遗言,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一天夜里,她和一名卫生员去船头接运伤员,当时敌人正向我阵地炮击,掩蔽部外火光闪闪。战友们都劝她俩等炮击停止后再走,但季悦想到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早一分钟接回,伤员就多一份生的希望,便冒着敌炮火出发了。当她俩接着伤员,开车行至天保农场时,一发炮弹在她们附近爆炸。为了不让伤员第二次负伤,她俩弯下腰,用身体护住伤员,直到安全返回。 和季悦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全队同志胆子变大了,思想变坚强了,危险地方都敢闯了,炮团榴炮二连开设前沿救护所,有人出于对她们关心说那里太危险。“正因为危险,连队的同志伤亡可能性大,所以更需要我们去救护,再说,连队干部战士能在那里战斗,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在那里救护?”大家下定了决心,把任务一宣布,全队人人报名争着去。 1月14日晚,副队长曹娟娟带领三名同志组成救护组,住进了榴炮2连防炮洞里。 15日,越对我发动大规模反扑,炮二连阵地上弹片横飞,硝烟弥漫。战士们冒着炮火顽强地与敌对射,救护小组的同志不顾战士们劝拦,穿梭在各炮位送药、巡诊,抢修被敌炸坏的工事,配合连队搞战地鼓动。 16日,驻地遭到敌人炮袭,炮弹就在帐篷前爆炸,大家刚钻进防炮洞,就听说外面一个单位五名战士负伤,伤情就是命令,救护队十几名同志奋不顾身冲向洞外,突然有三发炮弹落在离救护队五、六米远的地方。那一瞬间,大家根本没有想到卧倒,也来不及卧倒,幸好,是三颗哑弹。事后我们有的同志诙谐的说“敌人害怕我们女兵,飞过来的炮弹连气都不敢吭”!伤员抬进洞去,需要进行手术,可是器械和药品需到洞外手术室去取,麻醉医生张帆、卫生员张瑛,王剑霞三人又冒着炮火冲到一百多米外的手术室,取来麻醉药和手术器械,紧接着,我们在狭小的空间内,以担架为手术台,跪在地上进行手术,经过两小时奋战,使伤员全部转危为安。

薛晓军告别幼子(丹旗 摄)
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母爱,母爱的牺牲是最痛苦的牺牲。这话一点不假。她们当中12人是孩子的妈妈,当她们奔赴战场的时候,都经历过一番生离死别的痛苦斗争,都做出了舍弃母爱,放下娇子、共赴疆场的正确选择。军医薛晓军,女儿才半岁多,十分逗人喜爱。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她与在师机关工作的丈夫商量,准备将孩子托人照看,夫妻同上战场。有人对她说:你们就这么个宝贝,年纪又小,托人照看,就那么舍得?就不怕孩子吃苦?开始这话也曾搅得薛小军几晚上睡不着。有时夜里醒来好几回,流着眼泪抱着孩子亲了又亲了。但她懂得,幼小孩子需要我,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士更需要我。是部队把我送上军医大学培养的,我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部队出发那天,薛小军将孩子搂在怀里不停地亲吻着,两行热泪滴落在孩子脸上。她轻轻地对孩子说:别怪妈妈心狠,等打完仗回来,妈妈再好好抱你,千遍万遍地亲你。当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传来时,薛小军狠了狠心,毅然离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她想起心爱的宝贝,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更多孩子不失去母亲,妈妈的心,已不能把你牵挂;妈妈的爱,将化作那漫天彩霞,映红南国天涯。薛小军是内科医生,为适应战场需要,她虚心向有外科临床经验的同志学习,野战外科技术提高很快。她先后做气管切开、气胸封闭大小手术18例,全部获得成功。 17岁的卫生员唐兵花是救护队最小的成员,当第一次看到伤员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残肢时,吓得蒙住眼睛。在开展“为伤员、爱伤员”活动中,她懂得了应该以怎样的感情对待自己的战友,多次冒着炮火到前沿阵地接运伤员,平时护理伤员也不怕苦累。一次,她连续四十多小时没合眼,继续坚持抢救工作。三月八日深夜,前沿救护组的同志接回四肢被炸伤的战士张勇。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伤员十分痛苦,救护组的季悦和另一位同志就半蹲半跪在车厢里,用手托着伤员的双腿,并轻声安慰他。在一个多小时里,两个同志的腿蹲麻木了,双膝被车厢颠碰肿了,但她们一直坚持托着伤员到达我们驻地。
作者简介:

施劲松,江苏省射阳县人,1959年出生,1978年12月入伍,大学文化,历任战士、干事、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安徽省宁国市委常委、市人武部党委书记、政委,上校军衔,盐城市公安局副调研员、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盐城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三级警将警衔等职。1984年7月至1985年6月,参加老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师政治部组织干事。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