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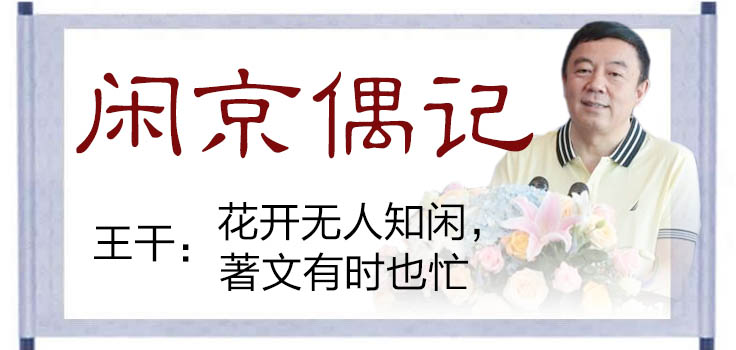
■王干 汪曾祺诞辰105年了。 高邮人研究汪曾祺得天独厚,高邮人研究汪曾祺理所当然,高邮人研究汪曾祺硕果已累累。如果把高邮人研究汪曾祺分为三代人的话,陆建华、朱延庆等前辈属于第一代,我和金实秋、陈其昌等大概属于第二代,金和陈这些年孜孜不倦,写了不少专题性的文章。而我写汪,研汪,编汪,基本是约稿逼出来的,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编辑,我算不上一个专心致志的汪曾祺研究者,之前零零星星地写过几篇,直至2017年出版社要出《夜读汪曾祺》《汪曾祺十二讲》,我才集中时间写了系列文章。 我不是高邮本土人,但因为在高邮学习、工作过,外界习惯称我为高邮人,或许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多次向人解释我本不是高邮人,但大家还把我和高邮联系一起。比如我多次向王蒙先生说我是高邮邻县的,但王蒙先生还是说我是汪曾祺老乡,我沾了高邮的光,准确说沾了汪先生的光。 近年来高邮研汪、全国研汪出现了新一轮的热潮,一些名家学者纷纷加入了研汪的队伍,郜元宝、王彬彬教授都有专著,其中郜元宝也是被约稿约出来的,当时我在《小说选刊》工作,推出了“经典回望”的栏目,汪先生的小说连续选了好几篇,《岁寒三友》《徙》的推荐文字是我写的,《星期天》的推荐文字我就请郜元宝写,有趣的是郜元宝之前居然没有看过《星期天》,看完以后,惊呼: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小说!本来让他写不超过六千字,他居然写近一万字,写完还责怪我不早点推荐《星期天》,我说汪曾祺的好小说多着呢!之后郜元宝开始刻意研读汪曾祺,并写了专著,字数远远超过我,这让我感到很惭愧,我接触汪先生那么久,写得那么少,还是能力和专注度不够。 汪研的第三波热潮中,除了郜元宝、王彬彬、王国平等外地学者外,高邮籍的翟业军、杨早、高邮的邻居苏北和远在山西的乌人以及高邮本乡本土的张秋红、姜文定、许伟忠、陆忠场、姚维儒等也频频写出新文、新著。陆忠场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他研汪的文字数量多,领域宽,层次丰富,涉及到史料、考据、鉴赏、评点以及整体美学精神的探索,可谓步步为营,呕心沥血,一些文章也被黑龙江、湖南的期刊选用,可喜可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高邮县政府大院与陆忠场相识,他在信访办工作,我在党史办上班,因为爱好文学经常有一些交流,发现他骨子里是很文学的人,是视文学为信仰、为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聊得来、处得来。陆忠场的名字带着浓厚的农耕色彩,“场”是打谷场,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显然是期待丰收、期待年景美好,当然也希望他辛勤耕耘、坚守庄稼的春种秋收,因而陆忠场骨子里还有一股韧性,一股牛劲,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这是他能够坚持读汪、研汪出成果的原因,汪先生天性佛系,但汪先生的文字经得起咀嚼,这让陆忠场的牛劲和韧性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释放空间——现代物理学称之为“场”。 陆忠场在读汪、研汪的时候坚持一种追求学术真相和真谛的精神。陆忠场不是学院中人,他的文章本不必笔笔交代出处,更无需事事求实,但他努力向学术看齐、向学者看齐,尤为可贵。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他在信访办的经历,信访工作对真相的诉求,也影响了他对汪曾祺的研究。他在用“访”的思维做文学写作和研究,他的文字追求“信”为上,对抗时下流行的浮躁和夸饰。 一个人影响了一座城,一座城又出了一群人,陆忠场是这一群中的一个,汪先生诞辰105年了,他的风范会被群之、众之、赞之、颂之。千古常常是对于一个逝者的套词,但一个人的作品被无数人和无数代人传播和“转发”,就是千古。
作者简介: 王干,出生于江苏里下河,现居北京。作家,学者,书法家。散文曾获鲁迅文学奖,著有《王干文集》十一卷。
来源:扬州发布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